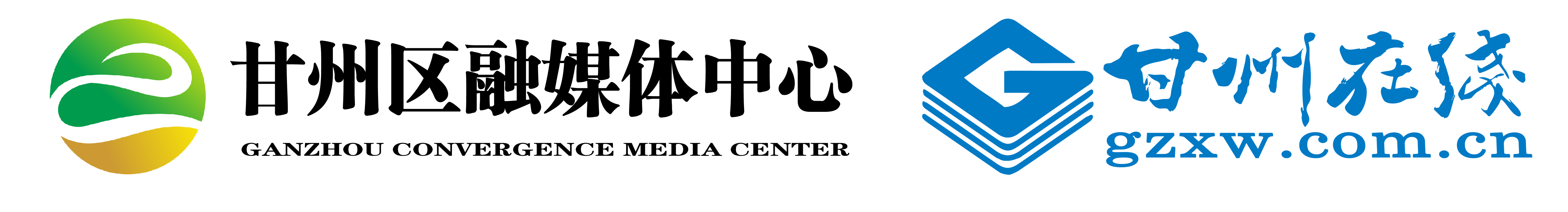看着春晚的繁华盛景,享受着朋友们漫天飞舞的祝福微信、短信,抢着群友们或多或少的红包,伴着新年敲响的钟声和室外此起彼伏的鞭炮,踩着寅虎年的祝福,往事历历在目。
偏爱宁静却无以致远,作为警察家属已习惯于独自守岁年复一年。儿子去采访甘州人民年三十的年俗节礼,不知道几点才能回来。为引导市民不要在大街小巷烧纸、抛洒祭品而污染环境,我们已经在寒风瑟瑟的大街上站了四五个小时,腿脚冰冷,整个人都麻木了。非常好的是市民都认识到了环境污染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,也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。都自觉到了指定的背街小巷焚烧抛洒祭品,不但支持了我们的工作,也给清洁工及时清扫带来了方便。
下午三点出门,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多,桌上没有杯盘,没有香羹,也没有糖茶与红酒,出门时只供了一盘干果和一碟油果子,什么饺子、水果、年夜饭之类的一样也没有准备。
许是冻得久了,浑身冰凉、头疼、流鼻涕,脸上也一阵一阵发烫,整个人恍恍惚惚的,进门倒在沙发上边眯了过去。
突然握在手里的电话响了,是妈妈打来的,问我吃没吃饺子,说等我等到八点多不见人,包好放在案板上了,怕太迟了路上不安全,就和爸爸先回去了。听到妈妈的声音,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爸爸妈妈已经七十多了,对儿女的牵挂还像小时候一样没有递减。看看手机已经是十一点四十,辞岁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,我支撑着起身去了厨房。一排排如银锭的饺子整齐地排在案板上,厨房窗台上供了两小碗拇指大小的薄皮供饺,这是妈妈多年的习惯,小时候家里再穷,年三十妈妈也会想方设法给我们包饺子,而敬奉先祖,尊老爱幼,邻里和睦、贤良淑德更是妈妈做人的态度,也是母亲教我们做人的道理。
打开煤气灶,下了一盘饺子,饺子皮薄馅绿,冒着蒸蒸热气,仿佛千锤百炼的银锭,历数千百年传承的美德,刻录着交子更替岁月静好。
突然左侧邻家响起了鞭炮,右侧邻家也响起了鞭炮,继而周边鞭炮齐鸣。望望窗台上被我捆绑在撑衣杆上的浏阳花炮,心头的怯意拂之不去。
小时候家境不好,买不起鞭炮,父亲就把雷管埋在门前不远的地里,拉一根长长的捻子(真不知道那捻子是哪来的),之后呵斥我们躲在门背后或是趴在炕头爷爷奶奶怀里,我们捂着耳朵,期盼那“轰”的一声巨响。好像从我懂事起,这样的巨响年复一年,直到有一年,父亲将珍藏了几年(具体几年父亲也记不清了)的雷管埋在门前的地里,拉上长长的捻子,继续将我们呵斥到门背后或是炕上爷爷奶奶的怀抱里,我们捂着耳朵,期盼着那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时针在一分一秒地旋转,“轰”的一声巨响却没有发生,我们已经按捺不住静候巨响的耐心,纷纷从门背后或是爷爷奶奶的怀里探出头来,站在我们身后的母亲继续呵斥我们,趴在院子里(许是捻子引线拉不到屋里的门背后)点火引线的父亲面前挡着一块厚木版,父亲匍匐着趴在木板后面,时针继续一分一秒地旋转,父亲也按捺不住,一边起身,一边骂骂咧咧地絮叨:“不可能啊!昨天我都烤好了,咋还是哑炮?”屋外漆黑一片,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灯之类的照明设施,家里最亮堂的要数父亲下煤窑使用的马灯了。马灯不但亮堂,而且能在风雨里摇曳不灭。
父亲回到屋里,点亮马灯,试探着朝埋雷管的地里走去,一步一探,父亲像是小心翼翼。母亲在门背后小声叮咛:“再等等看看响不响……”
爷爷也在炕头大声呵斥,不响就算了,看它娘的明天日头晒上响不响。
奶奶也大声呵斥:“急啥急,等到鸡叫了看它响不响……”
话音没落,一声怦然巨响,惊得炕头晃动,屋门摇晃,鸡鸣狗叫,响声过后屋里鸦雀无声,一秒、两秒、三秒,许是十秒……听不见父亲不急不缓的脚步声。
母亲突然大叫:“孩子他爹,孩子他爹,孩子他爹……”
爷爷一骨碌从炕上跳起。
父亲是单传,排行老三,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奶奶生下小姑姑后大出血撒手人寰,爷爷艰难地拉扯四个孩子,父亲七八岁时,爷爷续弦。后奶奶不生养,在前夫家领养了一个女儿,和二姑姑同岁,后奶奶对父亲姐弟不好,除了大姑姑(当年大姑姑十四五岁),对二姑姑、父亲、小姑姑打骂不断。
“文革”时兴批斗,后奶奶打骂父亲姐弟很厉害,大姑姑就到生产队告了奶奶“虐待儿女”,生产队派红卫兵把奶奶“请到”生产队接受教育,三天或是四天,后奶奶回来之后再没有打骂过父亲,不过,偶尔会打骂二姑,后奶奶的理由是,二姑嘴贱,不听话。总之,二姑挨打最多,小姑次之。
后奶奶喊叫声最响,“天杀的,不叫放炮不叫放炮,偏要放,那炮在窖里埋了几年了,这会子偏就响了。”说着推着跳起来愣在炕头的爷爷。
妈妈已经哭喊着跑出了屋子,屋子破旧松动的门扇被妈妈强拉开又合上碰撞得吱吱扭扭,院子里漆黑一片,妈妈惊慌的喊声穿透墨一样的夜色荡漾开来。
奶奶拄着拐杖,挪动三寸金莲已经跑到堂屋门口,爷爷依然在炕头岿然不动,姐姐趴在门边偷偷窥探漆黑一片的夜色,弟弟将头埋在被子里,我木然地盯着爷爷浑身颤栗。
时针一分一秒地旋转,一分一秒,院子里死一样寂静。妈妈的呼吸像幽远的神灵,在漆黑里回荡。
奶奶一步三晃,嘴里念念有词:天灵灵,地灵灵,保佑我儿活生生。天灵灵,地灵灵,保佑我儿活生生……
话音未落,院子里一声沉重的呻吟:“哎哟……”尾音长到银河九霄。
奶奶再一声谩骂:“这天杀的……”“咚咚咚”用拐杖敲击在破门板上。
母亲搀扶着父亲,一步一晃出现在昏暗的油灯下,爷爷默不作声,一下子瘫软在堂屋炕上。奶奶摇晃着身子,抚摸着灰头土脸的父亲,呵斥母亲快去拿红布披在父亲身上。许是红布尺寸不够,只够父亲半个脊背,奶奶又数落母亲,没有早备一块能够包裹父亲的大块红布。
父亲一脸惊慌,嘴里依然絮絮叨叨:“这天杀的,咋就响了。”
那一声巨响让我们全家四五年没再放雷管,直到家里能买得起鞭炮,三十晚上的炮声才又在贫穷而温暖的乡村小院里年复一年。
望着被我七绑八缠在撑衣杆上的鞭炮,四十年前的巨响历历在目。往昔点点滴滴在时光更替交互中幻化成千言万语,如涓涓细流融会在生命无线的长河之中,生生不息。
历历在目的还有荒滩野草丛生,涓涓细流清澈见底,田间泥土清香,果园里虫蚊嘤嘤,蚯蚓在泥土间穿行,蝴蝶在野花中舞蹈,蜻蜓在池水里嬉戏。远望祁连雪山苍翠清幽银光灿灿,草原碧波荡漾,牛羊闲庭信步,这些美好的景象恍如隔世。